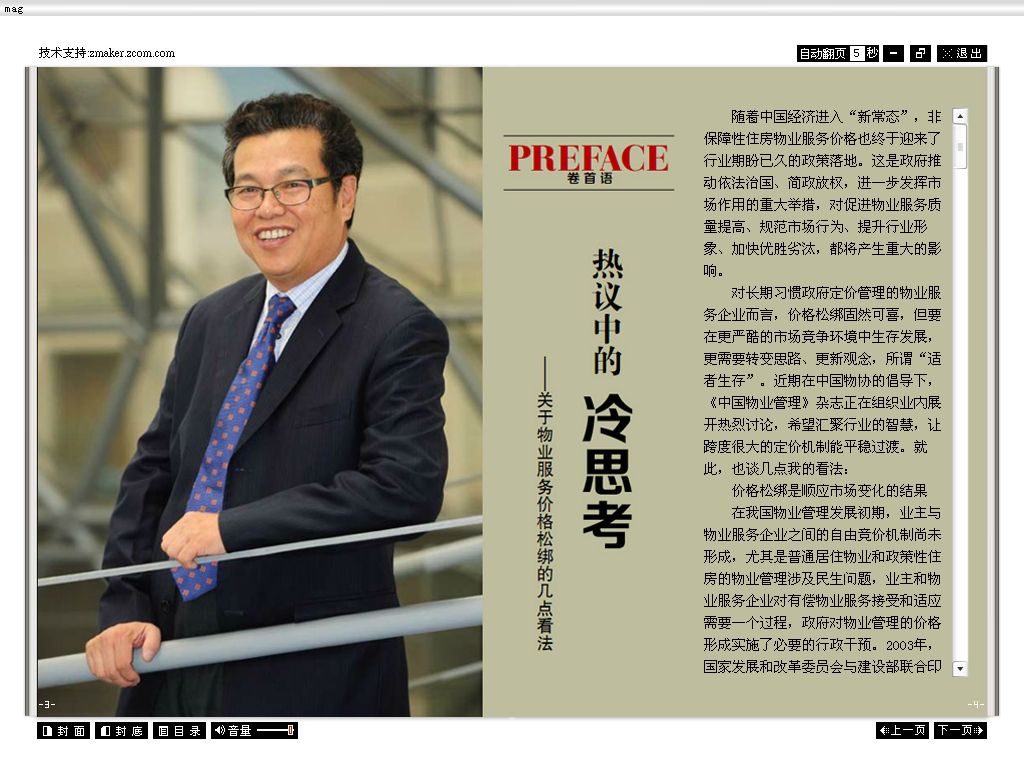刘闻皓:过马路,原来可以这么复杂
自1995年6月1日,上海市文明委发布“七不”规范以来,“不乱穿马路”便被定义为一个都市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可是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尽管马路越来越宽、管理人员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完善、管理设施越来越先进,可惜乱穿马路的行人却没有与此成反比。过马路,一个简单的问题,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行路难,行路何其难?马路归谁使用?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是承担马路修建费用的主体,同时也是马路的使用主体。现代都市修建的马路不是供行人使用的,行人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马路的“过客”。因为行人几乎不在乎有没有马路,正如鲁迅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所以行人自然成为马路上先天的弱势群体,一个“过”字就清晰的对行人所处的状态作了定位,马路更多的是对行人行为的限制。
马路“立法”的目的是什么?
这种先天的弱势,更表现在立法上。马路“立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提高通行效率。以马路作为载体的通行效率,其实更多的是在牺牲行人通行效率的前提下,来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马路,行人可以免去“一停、二看、三通过”,也不用“急吼吼”的赶绿灯,要大步流星还是闲庭漫步你随意。这一点也充分揭示了法的本质之一,法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法不责众”这一民间思维惯性在马路立法中刹车了。
成本知多少?
既然“法要责众”,司法成本也就水涨船高了。以本市为例,由于本市警力资源不足,自2000年上海城区开始增设交通协管员(其管理的主要对象是行人和非机动车),目前一个区的交通协管员就达500名,估算下来,整个城市的交通协管员大体有5000人。据了解,上海的交通协管员月薪是900元。按此计算,单工资一项,全市每年要投五千多万元。按照1600万人口计算,如果每人每天闯一次红灯,那么每闯一次红灯,城市管理就要额外付出1分钱。这还不包括交警的工资和其它设施设备的投资。
效果如何?
投入是巨大的,收效却是微弱的。多年来我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数均超过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还以本市为例,去年本市共查处行人、骑车人交通违法行为249万次,占交通违法处理总量的28%;因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导致382人死亡,约占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
据估算,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造成每人每天用在交通出行的时间多损失20%。按目前每位市民每天用于出行的时间平均为1小时40分钟,这20%换算成具体时间,便是每人损失20分钟。
背后的动因
行人乱穿马路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会说是文化成因,而我认为,马路的建设、管理是伴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而发展起来的,拿别人二百多年的汽车文化和我们至今才有几十年,并且是舶来的汽车文化相提并论是显失公平的),如果在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理想状态,我认为,主要是受到价值排序的影响。
秩序
交警、协管员、红绿灯等,目的是维持正常的通行秩序,应该说,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秩序是首要价值。一个具有通常道德水准的人应该具有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引自己的行为。所以在没有其他因素下,稍具道德的人都会选择遵守秩序。
效率
前面已经分析过,行人是马路的“过客”,所以遵守秩序则要牺牲效率。以我为例,闯红灯的几次都是由于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要赶时间,也就是为了效率。为了效率,我选择了不要秩序。因为,效率的价值排序在秩序之前。相信多数人的行为选择也是如此的。因为着急回家、着急办事,只能选择乱穿马路。
金钱
有时候在效率和秩序之间可以进行价值转换。按新出台的交通法规,乱穿马路可以予以5~50元的罚款。违法的成本增加了,资金杠杆就会对部分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上班迟到二分钟要扣30元,而闯一次红灯要罚50元,我自然就选择作个文明市民。但对于两种类型的群体,会令“金钱法则”失语。一种是没钱的主,正所谓无钱者无畏,我身边就2元,要不要随你;另一种是相对有钱并且视效率为生命的主,有一个故事正好说明这个问题,比尔盖茨假如不小心把1000美元掉在地上,他是不会去捡的,因为他一年能赚78亿美元,这一弯腰的时间已经够他赚回1000美元。
自由
如果闯一次红灯,将被拘留10天,那么还有没有人闯红灯?回答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无论多么紧急的事情,和拘留10天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看来,自由的价值排序在金钱之上。排在自由价值之上的还有生命的价值,如果不乱穿马路,可能命都保不住(譬如有人在追杀你,或者如果办不好某件事就可能送命),那还会不会乱穿马路?当然是闯了,和命比起来,拘留又算什么?
事实上,乱穿马路是威胁到行人的生命权,但是这对人们行为约束力很微弱,因为这是隐形的威胁,并且常人都有趋利的心里暗示,就像尽管交通事故的发生率要远远高于福利彩票中奖率,可是人们习惯于谋划着中奖后的资金分配问题,却很少考虑到乱穿马路的后果。
敢问路在何方
秩序、效率、金钱、自由,有了这样的价值排序,我们就可以从立法层面或规划层面解决一些问题了。
以人为本和以人为先
首先应提高行人的通行效率,以“以人为本”的思想来规划、设计、管理道路,保障行人的权利。国外的研究结果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30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就有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后果,以本市的内环线为例,不少地段都使用上了绿化隔离栏,可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却不多,有时候为了“文明”不得不付出六、七百米的脚力。
“以人为本”不仅仅应该是口号崇拜。
现在本市机动车道是越修越宽,但是行人和骑车者的路越走越窄,特别是为了解决车辆交通问题而拓宽道路,就拿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开刀,非机动车道一再被挤,而行人有的就根本无路可走,根本不考虑行人的权利和安全。人们老是指责自行车停车占用人行道,可是道路建设者有没有考虑过,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如此之窄,自行车该往哪放呢?人为地剥夺一种交通工具的空间,反而会带来它们对有限空间的互相侵占,让交通更无序。
立法保障和立法有效
其次从立法上来保护行人的权利。早在1964年,德国就制定了行人过人行横道时司机必须遵循的法律条文:只要行人在正式人行横道上行走,司机必须以合适的速度行驶,不得危及行人的安全,必要时停车,禁止与行人抢道。司机在人行横道处要超越前车或从其旁边驶过,必须以不危及行人为前提。人行横道处5米内禁止停车,包括临时停车,因为停住的车辆可能会挡住其他司机的视线,同时行人有可能在这一区域内横穿马路。为了防止行人“过分使用”这一优先权,法律也相应规定:行人不得随意穿越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
当然,还要考虑立法的有效性。最近对行人乱穿马路的治理导向偏重于行政罚款,罚款属于管理中的负强化,往往治标不治本。前面已经分析过,自由的排序在金钱之上,不过不是简单的拘留。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一向以严刑峻法着称,对于乱穿马路的行为不是“一罚了之”,而是惩罚其扫大街,至少两个小时以上,行政收入不高,行政收效却很高。还有美国,不论何种交通违章,只要被开具罚单和接受处罚,违章记录即永久性地存入个人有关档案中,这些记录对本人晋升、信用、保险、求职等方面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想保持安全记录清白,唯一的途径就是遵守法规。这些都是变通的自由限制,其效果远远好于罚款。本市前段时间也有过类似的举措,就是让违章人士做协管员,直到下个“顶包”人士的出现,但不知道为什么无疾而终了。
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
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除了价值排序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司法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公安部曾对上海的交通秩序进行了3天的暗访,机动车的遵章率达到了99%,而自行车和行人的遵章率不到50%,这就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万的自行车和行人违章,而绝大部分违章并没有受到处罚。
交警为什么对行人违章爱理不理?一是当机动车、自行车、行人密度非常大,并纠缠在一起时,处理违章成本也大,也就是说当交警处理违章的同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违章,交警自然倾向于选择不处理或少处理,而这又导致违规收益很容易大于其成本,人们更倾向于违规,从而出现恶性循环。二是交警的收入与罚款挂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样的管理无疑是鼓励行政权利寻租,现在对司机敬个礼,起板五十,一般二百,对行人敬个礼,少则五元、十元,多则一脸唾沫,也难怪交警把机动车辆作为违章处罚的主要对象。而交通协管员和我们物业管理从业人员一样,只有劝阻权、警告权而没有执法权,吹吹哨子、练练嗓子,全靠父老乡亲捧个场,实现的只是“稻草人”效应。
离开有效的司法,再完美的法律法规都只能存在于纸面之上,没有丝毫意义,而单纯依靠个人的道德水准来维持秩序,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是不可能的。
结语
过马路,一个小而平常的问题,却可引发如此多的思考,这让我想起佛教里的一句话:一叶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思考有时候显得多余,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细微处入手,从自身做起,从过马路开始,来构建“马路上的和谐”。
文章中引用数据摘自《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三联生活周刊》。
-
深圳福田区住宅小区疫情防控工作标准化手册培训资料 44552

-
疫情之下,决定你生活水平的不是房子,而是物业!业内关注 48790

-
“职业物闹”,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物业要警惕、政府要重视、公安要严打!业内关注 155358

-
热议中的冷思考——关于物业服务价格松绑的几点看法业界评论 43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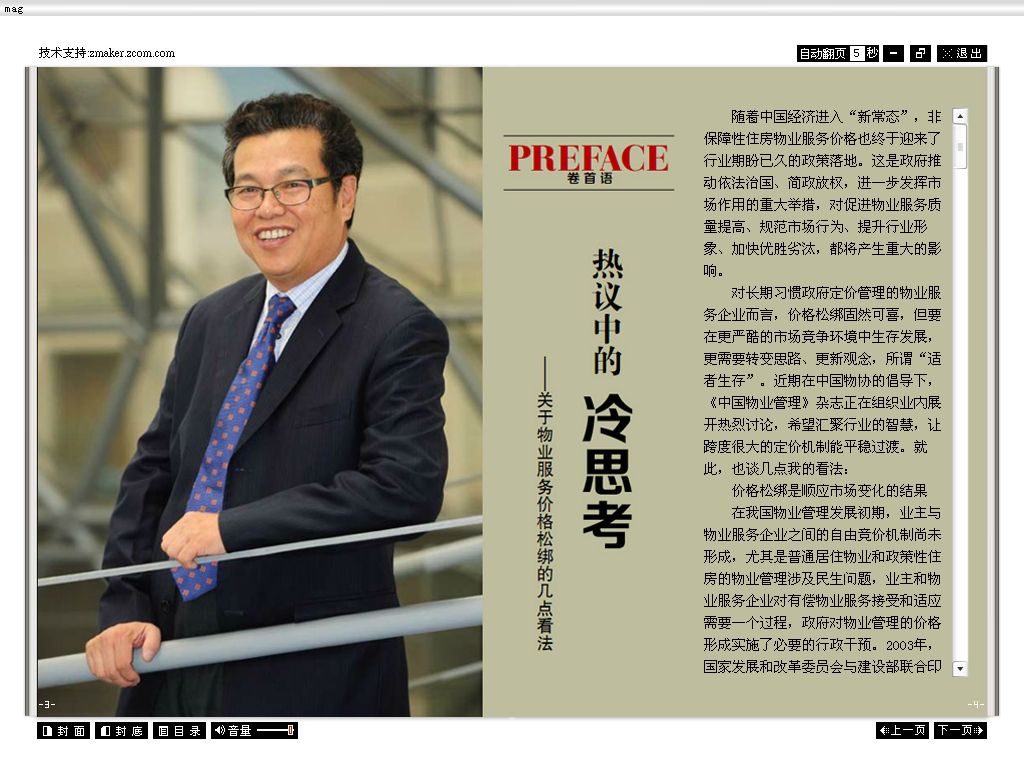
-
沈建忠:为“标准建设年”定基调专家访谈 58805

-
物业管理行业未来的三个基本判断业界评论 137049

-
保姆纵火案遇难家属起诉绿城物业和消防 杭州中院正式受理业内关注 63612

-
新修订《安庆市物业管理办法》亮点解读政策解读 31569
-
池州市引入仲裁机制破解物业收费难业内关注 28370

-
未按时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深圳59家物业企业上“黑榜”业内关注 30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