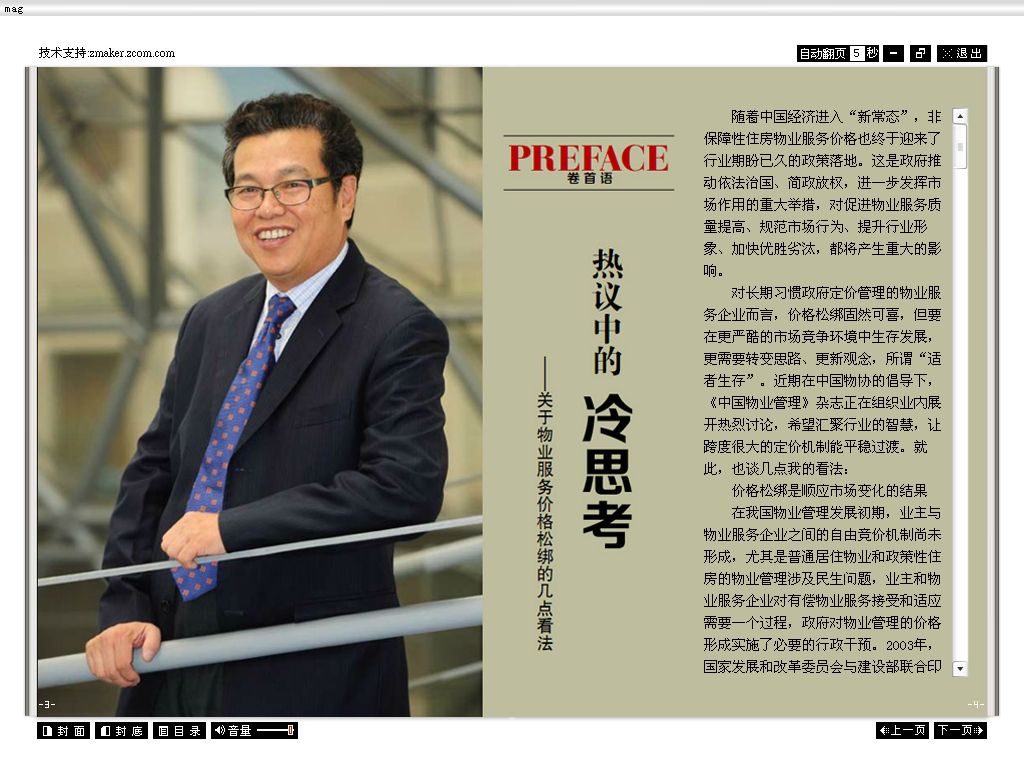社区行政化还是自治化?从现状看未来
孙中山先生面对的理想与现实,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富强,民主,文明,这是我们新时代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遭遇的现实处境却让我们常常困惑不已。在上海,城市居委会这个网络被视为行政管理的第四级网络,与市政府、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这三级网络相联接。从民主建设的角度看,居委会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核心阵地,而基层民主建设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个角度讲,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在社区管理的现实中,诸多不和谐偏偏是因为二者关系处理不好或者这二个组织本身的建设与管理就存在交叉、矛盾或者逻辑不清的问题。任何社会组织,在权力合法性或者运行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话,指望它能把社会治理得天时、地利、人和,那等于痴人说梦。
最近有两个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以及有关社区管理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思考:
第一个引起我关注的事件是此前不久发生的通钢工人打死总经理的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目前尚没有最终的一个结论,但是从《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以及《瞭望》的相关调查、网络的热议来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共识和压力。不管对政府管理者还是企业组织,这都是值得警醒的大事件。这个事件可能提醒我们对基层群众组织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即作为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在工厂治理变迁过程中到底发挥过什么作用?很明显,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整个事件,我们看不到工人与工厂沟通的合理渠道,看不到工会这一本该由工人自发形成的群众自治组织或者维权组织,哪怕履行一丁点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由这个事件,我们来看我们当前的社区管理,如果我们把一个社区看成一个社会管理单位,那么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恐怕比任何社区行政组织建设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那么,对社区而言,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具体指哪个组织呢?是居委会,还是业主委员会?
如果我们把中国当前社会的政治组织架构作一个层级或者网络分析,我们会发现,自《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以来,我们的二元社会体制其实存在着一一对应和内在的管理逻辑。或许建国的前辈们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共和国,取得政权之后,此前治理农村的经验远远比治理城市更加丰富,于是在立法、执法以及政治组织方式上,习惯于将农村的治理经验直接移植到城市。
从《宪法》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的精神讲,居委会应该属于“三自”性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而非行政单位,但目前的现实情况又是什么呢?这里的“自治”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但是在1958年之前的社会政治架构中,居委会的面貌和存在形式与目前大不相同,虽然那是计划经济环境下的产物,但至今依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上海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在1998年完成的《居委会自身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的研究报告中作了这样描述:“解放初期到1958年,居委会是典型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居民委员会干部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和治保主任、妇代主任、福利主任都不拿津贴、义务工作。不少在职职工、在学高中生,业余时间也爱往居委会跑,大家将居委会当成家。当时,工厂、商店等招工机会很多,居委会干部宁可不拿一分钱,整天在居委会义务工作,却不愿进工厂、商店去干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其原因是担任居委会干部有光荣感。解放初期的居委会还没有建立党支部,居委会工作主要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办事处的干部三天两头在居委会,与居委会干部一起工作。当时居委会工作大多根据居委会辖区内的居民意见、要求来确定,如组织居民义务劳动,改善居住环境。该时期居委会主任和其他居委会干部在居民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由于居委会干部长年累月与居民群众在一起,所以,几乎每家每户都认得居委会主任,有的年事高的居委会主任几乎成了居民群众的‘老长辈’,家里事、邻里事、里弄事,都会找居委会主任反映,请示居委会干部帮助解决。居委会干部与群众关系融洽,因此,居委会换届改选、推荐候选人等选举工作开展也比较顺利。”
但随着58年之后的持续“折腾”,居委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却逐步遭受行政化的侵蚀,随着历史演进,最终形成了目前居委会更看重对上负责,不对居民负责的管理现状。在社区居民开始关注社区、参与社区和影响社区的趋势下,居委会的行政化到底是出于社会治理不得不为的无奈?还是出于我们社会在治理思维上的落伍?在这里我们很难下结论,但是,如果从实践来看,目前居委会的行政化不仅削弱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内在自治性,而且还影响了公众对社区管理的冷漠化,这可以从居民对居委会选举热情不高的事实中得以说明,而很多地方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又似乎非常的嚣张跋扈、只看权利、不看义务。
居委会的行政化侵蚀,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一时难以改变的一个社会存在,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原因一是因为我们的历史遗产,毕竟我们从计划经济走来,民众习惯于被管、被组织的意识遗留过于丰厚;原因二是因为我们的转型环境,不当头、鸵鸟心态、政治冷漠,这些潜意识促使民众对公共权利的关注、对公共环境的关注非常淡漠;原因三是因为我们的民主训练不够,以为自选一个组织出来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就可以不懂装懂,就可以对物业企业颐指气使、或者对于外在行政管辖或者社区以外的事务不闻不问。以上诸多理由,为居委户的行政化创造了历史条件,也可以这么说,宪法所阐述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立意很好,但目前的实践还存在非常遥远的距离。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将发展包括基层群众自治在内的基层民主作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底这里所说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以居委会为载体还是以业主委员会为载体,还存在巨大的法律想象空间。
第二个引起我关注的事件是深圳新市委书记王荣走马上任,动作利索,快刀乱麻,短短时间内就出台了大部制改革,而且还精简了1000余名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具体是什么层级的公务人员呢?新闻报道说,“区、镇、街道办和社区也会有一部分人下岗”。区级管理、街道委派、驻扎社区,是目前社区管理的行政组织现状,深圳的精简举措是否能看成加强基层群众组织自治的一种先导呢?不同的人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笔者不想做具体展开。
之所以闲言碎语讲这么多,其实和我们物业管理的发展关系密切,因为如果我们遵循十七大报告的引导看我们未来的社区管理,我相信在一个权责清晰的环境中开展服务,更有利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市场化运作,因为一个清晰的权责网络,至少能让我们删繁就简,清楚地知道客户是谁?负责什么?对谁负责?只有这些关系理清楚了,我们的社区管理才会免除一级对一级的歧视,避免一级又一级的不作为。
或许有人会说,指望当前的业主组织进行社区自治,绝对是讲笑话,或者即使自治了,也是先天不足。我则这么看,如果我们从行政化的侵蚀中看到的是社区的死气沉沉或者活力不足,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改变付出一些代价,你不培育它走向自立,它就会永远赖在行政管理的“怀”里,而且还充满怨气,不能再这样娇惯下去。精神上孱弱惯了,即使白白胖胖,也必然是扶不起的阿斗或者银样镴枪头。这就如同小孩,十八岁之后必须扫地出门,否则,他们只会永远趴在地上、永远嗷嗷待哺,生命的自立、自强规律显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深深的期待。
-
深圳福田区住宅小区疫情防控工作标准化手册培训资料 44552

-
疫情之下,决定你生活水平的不是房子,而是物业!业内关注 48790

-
“职业物闹”,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物业要警惕、政府要重视、公安要严打!业内关注 155358

-
热议中的冷思考——关于物业服务价格松绑的几点看法业界评论 43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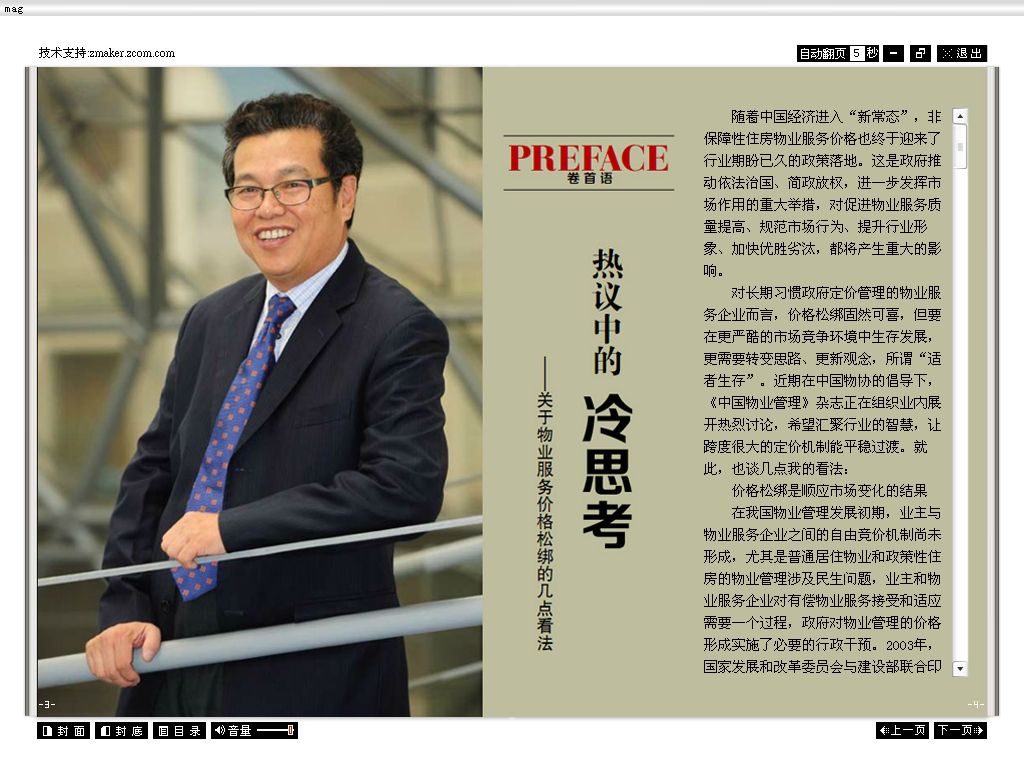
-
沈建忠:为“标准建设年”定基调专家访谈 58818

-
物业管理行业未来的三个基本判断业界评论 137049

-
保姆纵火案遇难家属起诉绿城物业和消防 杭州中院正式受理业内关注 63612

-
新修订《安庆市物业管理办法》亮点解读政策解读 31569
-
池州市引入仲裁机制破解物业收费难业内关注 28370

-
未按时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深圳59家物业企业上“黑榜”业内关注 30931